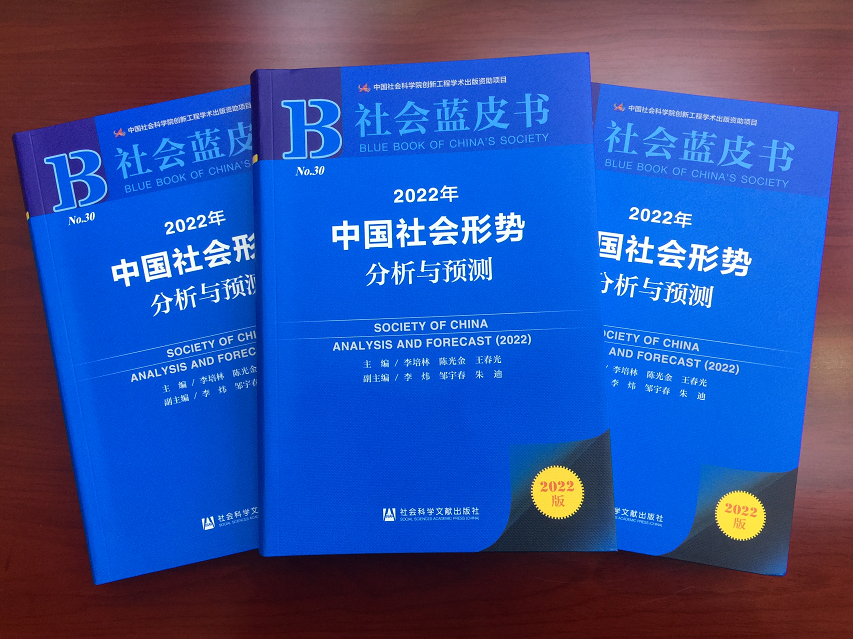【中國社會科學(xué)報】呂鵬|宏觀社會形勢分析:宏觀形勢的另一張晴雨表
2023-02-16
2022年中央經(jīng)濟(jì)工作會議提出推動經(jīng)濟(jì)運行整體好轉(zhuǎn)的目標(biāo)。隨著“兩會”的臨近,對宏觀經(jīng)濟(jì)形勢的分析成為各界關(guān)注的熱點。眾多權(quán)威機構(gòu)和專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和分析,也引發(fā)了較大的關(guān)注和反響。然而,在這些討論中,對宏觀社會形勢的判斷卻顯得相對不足,如認(rèn)為其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關(guān)系不大而將其忽略,或把社會問題理解為就業(yè)、勞動、醫(yī)療問題而主要從經(jīng)濟(jì)角度討論,抑或雖高度重視宏觀社會形勢卻因各種原因未展開實質(zhì)分析。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缺席,讓我們在觀察宏觀形勢時缺少了另一雙敏銳的眼睛;而對宏觀社會政策討論的不足,尤其是與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的討論脫節(jié),則讓經(jīng)濟(jì)政策的落地,缺少了更加堅實的社會基礎(chǔ)支撐。
社會形勢影響經(jīng)濟(jì)發(fā)展前景
日益復(fù)雜的社會形勢,已成為影響甚至制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可忽視的力量。早在20世紀(jì)90年代,李培林就提出,社會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是影響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資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它既是經(jīng)濟(jì)增長的結(jié)果,也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從社會結(jié)構(gòu)的角度來說,以婚姻、生育、養(yǎng)老為代表的人口變化已是各界討論的熱點,不僅直接牽動社保、教育、醫(yī)療等社會政策,也對勞動力供給和人力資源素質(zhì)等產(chǎn)生重大影響,從而直接影響經(jīng)濟(jì)發(fā)展前景。但是,社會結(jié)構(gòu)的問題絕不僅限于“人口結(jié)構(gòu)”這樣的顯性議題。比如,我國整個社會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發(fā)生重大轉(zhuǎn)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成為縮小收入差距、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guān)鍵所在。但社會流動狀況并不樂觀,給更多人創(chuàng)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fā)展環(huán)境任重而道遠(yuǎn)。
一些社會問題,在部分領(lǐng)域和時點,甚至?xí)蔀橛绊懡?jīng)濟(jì)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主要矛盾。以近期大家最為關(guān)心的預(yù)期為例,一些企業(yè)家信心不足、投資意愿不強、瞻前顧后,一些民眾消費意愿不足、焦慮感卻十足,“躺平”“內(nèi)卷”同時成為熱詞。這些已經(jīng)不僅僅是個體心理現(xiàn)象,而是一種社會心態(tài)?;膺@種社會心態(tài),就絕對不僅是一個經(jīng)濟(jì)政策的問題,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政策的問題。這些社會政策也不僅是民生、就業(yè)、醫(yī)療等領(lǐng)域的兜底式問題,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如何在社會領(lǐng)域化解社會失范、重建社會團(tuán)結(jié),在社會領(lǐng)域開展“宏觀調(diào)控”,實現(xiàn)整個社會有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建設(shè)式”問題。
完善社會形勢研究體系
社會學(xué)界30多年來開展的一系列社會形勢分析與預(yù)測研究,呼應(yīng)了時代的需求,影響力持續(xù)不衰,為更高水平、更強整合的宏觀社會形勢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從1992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社會學(xué)研究所每年都圍繞“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yù)測”這個課題組織精干力量開展研究,發(fā)布的年度《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yù)測》(“社會藍(lán)皮書”)已經(jīng)成為國內(nèi)最有影響力的宏觀社會形勢報告集。正如李培林指出的那樣,“課題組對社會形勢的分析與預(yù)測,之所以沒有出現(xiàn)大的誤判,就是始終堅持準(zhǔn)確把握發(fā)展大勢和辯證的視角,既看到發(fā)展的成就,也看到發(fā)展的問題”。這種視角也貫穿在社會學(xué)研究所一系列的其他宏觀報告中。陸學(xué)藝領(lǐng)導(dǎo)的團(tuán)隊關(guān)于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曾引發(fā)廣泛影響,社會心態(tài)研究的影響力也日益壯大。現(xiàn)在,社會學(xué)家們有了更加先進(jìn)的分析工具、更加豐富的數(shù)據(jù)資源,應(yīng)該拓展學(xué)術(shù)研究的鏈條,在社會結(jié)構(gòu)和社會心態(tài)的宏觀分析上做出更有政策和社會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在諸如收入分配、財富積累、社會保障、共同富裕、社會流動、社會心態(tài)等議題上發(fā)出更加響亮的聲音。
現(xiàn)有的宏觀社會形勢分析依然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升級改造,從而適應(yīng)新時代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需求,成為與宏觀經(jīng)濟(jì)形勢并駕齊驅(qū)的研究領(lǐng)域。第一,“社會”依然是一個龐雜的模糊領(lǐng)域,對宏觀社會形勢的分析缺乏一個整合性的框架。民生、福利、教育、醫(yī)療、環(huán)境、人口甚至輿情,都可被看作“社會”,但又各成體系。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宏觀社會形勢分析中,在微觀領(lǐng)域同樣存在。比如ESG評估,雖然S(社會)是其中一個要素,但對S的量化評估是最為混亂和最為模糊的,讓真正的社會價值評估的效果大打折扣。第二,對宏觀社會議題的研究不足。雖然有“宏觀社會學(xué)”這一概念,但學(xué)科化程度嚴(yán)重不足,有時只是變成了“宏大敘事”卻沒有堅實的實證支撐。而實證研究越來越沉迷于“微觀旨趣”,一些學(xué)者呼吁的“宏觀轉(zhuǎn)向”尚未成為主流。第三,宏觀社會形勢分析尚未建立起與宏觀經(jīng)濟(jì)形勢分析類似公認(rèn)的、成套的指標(biāo)體系。與諸如GDP、CPI、國際收支、固投指標(biāo)等不同,宏觀社會形勢的分析還缺乏認(rèn)知度高、政策指向明顯的指標(biāo)。而對諸如失業(yè)率、就業(yè)率、基尼系數(shù)這樣帶有社會意涵指標(biāo)的測量,往往也成了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工作。第四,宏觀社會形勢的分析往往善于以年度和年代為單位的中長期的回顧和總結(jié),很少開展以季度甚至更短時間為單位的短期的研判和預(yù)測。近些年來,隨著大數(shù)據(jù)的日益豐富和技術(shù)的升級,以輿情分析、社會風(fēng)險分析為代表,一些場景取得了單點突破,社會預(yù)測研究也方興未艾,但整體上離國家、市場和社會的期待依然有較大距離。
為此,需要加快建立支撐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學(xué)術(shù)體系、學(xué)科體系、組織體系和政策體系。第一,應(yīng)對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理論框架、指標(biāo)體系等關(guān)鍵學(xué)術(shù)問題開展研究。宏觀社會形勢分析,不僅要能拿得出一篇篇有力度的專題研究報告,而且這些研究報告還應(yīng)該在一個整合的框架內(nèi)形成自洽的理論邏輯體系和豐富的指標(biāo)體系。第二,應(yīng)加快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學(xué)科體系建設(shè)。目前,有意愿、有實力從事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專業(yè)科研機構(gòu)還不夠多,一些專業(yè)機構(gòu)內(nèi)部也未能形成專門的、穩(wěn)定的研究團(tuán)隊,在人才建設(shè)、數(shù)據(jù)庫建設(shè)、硬件建設(shè)上存在較大短板,甚至與一些市場化機構(gòu)的差距也在拉大。第三,應(yīng)加強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組織保障。就如同宏觀經(jīng)濟(jì)形勢的分析主要和最終是政府相關(guān)部門的一項重要工作一樣,宏觀社會形勢分析也應(yīng)該進(jìn)一步加強組織協(xié)調(diào),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統(tǒng)計局、民政部、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等部門應(yīng)通力合作,形成具有標(biāo)志性的成果。同時,考慮到一些社會數(shù)據(jù)的敏感性,應(yīng)建立起符合國家利益的搜集、分析、使用和發(fā)布機制;在一些指標(biāo)上,鼓勵第三方科研機構(gòu)先行探索。第四,應(yīng)加強具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社會形勢分析的政策體系建設(shè)。宏觀社會分析既要可以進(jìn)行國際比較,同時也要進(jìn)一步統(tǒng)籌發(fā)展與安全,協(xié)調(diào)經(jīng)濟(jì)政策與社會政策。突破和超越傳統(tǒng)的社會政策領(lǐng)域和模式,夯實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社會基礎(chǔ)和觀念基礎(chǔ),將是實現(xiàn)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一招。
(呂鵬,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社會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重大創(chuàng)新項目“共同富裕的階段性衡量標(biāo)準(zhǔn)”階段性成果,載于《中國社會科學(xué)報》2023年2月15日第5版)